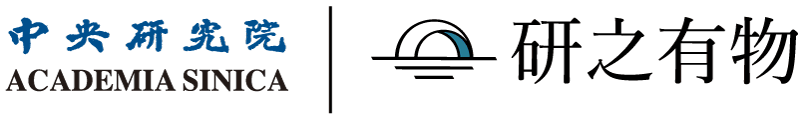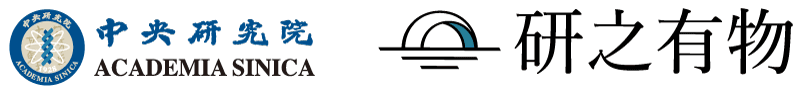圖│研之有物
 巫文化中,感到最不可思議的現象?
巫文化中,感到最不可思議的現象?
在排灣族的巫文化中,有一個成為女巫師 (puringau 或 marada) 必需有的「物」,引起我很大的研究興趣,那就是稱為 zaqu 的「巫珠」,有的排灣地區發音為 za’u 。
巫珠是神靈的代表,也具有與神靈溝通的功能。巫珠的外形很像無患子樹果實的果核,但對於女巫師而言,這不是無患子果實的果核,而是神靈界的創造者或巫祖賜予自己具備成巫資格的認證,絕非巫師自己在樹叢撿來的。

圖│胡台麗提供
古樓村兩位最資深的巫師 Muakai Tjakivarit 和 Laerep Pasasav 表示她們使用巫珠時,主要為了三種目的:卜問部落的男祭司人選、卜問病因和死因及用何種方式處置、處理喪事時作為護身符。
巫珠出現的情境非常神奇,例如:望嘉村的 Qalsirh Jangerits 巫師( 1921 年生)生下來時手握著打不開,請鄰居老人家拿豬骨祭拜,手指才舒展開,並看到一顆巫珠。春日鄉力里、七佳、望嘉部落、與來義鄉白鷺部落,認為如果女子身邊出現巫珠而不願成為巫師,那麼她本人或家族會有病痛禍害,但另一些排灣村落則沒有這樣的說法。
並非成長經驗中有獲得巫珠的女子都能成為巫師,排灣族認為,拜師習巫的排灣女子即使之前已有巫珠出現,但若在她的成巫儀式唱經過程中,沒有一顆巫珠降下,她也不能成為巫師,意味著沒有獲得神靈的認可。
在古樓村的成巫儀式中,會用竹籃、甘蔗搭成橋,上面放粗麻繩或麻織的布條,再鋪上苧麻纖維和荖藤葉,並把一大片香蕉葉插入接近天花板的窗縫,作為巫珠降下的通路。參加的巫師每人手持一把苧麻和桑枝葉開始唱經,接著要成巫的學徒進行昏厥儀式 (kiringats) ,腋下夾麻布、繞東邊竹籃爬行五圈後昏倒。
當學徒被喚醒後,若腋下夾的麻布打開後有出現一顆巫珠,就認定該學徒的巫師身份。排灣族女巫師在部落中負責許多集體性和個人性的祭儀,受到很大的尊重。
在田野遇到「物」時要保持天真和開放的心態,讓「物」展現自己,而不是迅速認定該物代表什麼。
 有沒有女巫看得到的「東西」,是老師研究時看不到的?
有沒有女巫看得到的「東西」,是老師研究時看不到的?
在噶瑪蘭人今已失傳的 kisaiz 成巫儀式中,年紀較長且經驗豐富的 mtiu 女巫們,會從女神處 ka-saray 拿下來一條「神靈線 (saray) 」,撒出去密密麻麻地纏住新巫(要治病成巫的女子)的手腳,象徵性地穿入新巫體內。
當新巫手腳被神靈線綁住、不能再走動時,她會象徵「死亡」昏倒在地,看起來像喪失意識,代表新巫已經順利抵達神靈所在之處。接著,比較有能力的女巫會在旁喚回昏倒的新巫,當靈魂回來表示新巫獲得能力再生,展演「死後復生」也代表為部落帶來新生命。

圖│劉璧榛提供
 兩位老師如何接觸到原住民的「巫文化」?
兩位老師如何接觸到原住民的「巫文化」?
我是南投鹿谷人,在很典型的漢人父系大家族長大,雖然國中時有接觸到布農族、泰雅族的老師,但真正讓我開眼界是,大學時到花蓮吉安鄉東昌村的阿美族 Lidaw 部落家庭裡,看到家庭裡的女人講話很大聲、意見很有份量,和我的家庭很不一樣。
阿美族的媽媽氣勢很不一樣,很辛苦地做事情,也很有權力和地位。讓我想到我阿嬤跟媽媽即使拼死拼活地努力工作,在家裡也沒有什麼份量,都是阿公或爸爸在做主。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文化震撼,只是跨越一個中央山脈,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後來我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 (E.H.E.S.S.) 讀社會人類學及民族學的時候,我的老師寫了一本關於男性支配的書,探討在經濟階級不平等前就已存在的性別不平等。於是我的論文思考母系社會中男女是否較平權,女性擁有哪些權力?特別看噶瑪蘭社會如何生產出「女性巫師」,解析其性別的政治宗教性。
在巫文化中,最顯著也最讓人好奇的就是女巫會做很多儀式,這是外人看起來會霧煞煞的地方,因為越霧煞煞,就顯出其文化的差異性。更不一樣的是女巫都是阿嬤,在儀式中很有活力地唱歌跳舞,儀式常常從一早做到半夜,體力都比我還好。
台灣民間常見到乩童多是男性主導,但原住民的巫文化中幾乎都是女性掌舵,我很想進一步探究其差異原因。
我讀臺灣大學歷史系的時候,很喜歡去修一點人類學系的課,尤其是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讓我非常好奇。因為以前歷史系的訓練多為埋首古籍,但田野是人類活生生的生活場域,可以接觸不一樣的文化。
我第一次參加田野調查,是跟著臺大人類學系暑期營隊到卑南族的部落。卑南族是「從妻居」的社會,丈夫結婚後住在妻子家裡,門牌的戶長都是妻子的名字。在卑南族的部落裡,我看到我寄住的家庭中妻子拿著雞毛撢子在院子裡追趕先生,是漢文化中不常見的視覺衝擊。阿公(妻子的父親)也跟一家人住在一起,這種家庭結構和我們不太一樣。卑南族人說話語調、動作和表情都很幽默,而漢文化比較壓抑。這些文化差異,讓我覺得文化充滿可能性和變異性。
在自己的文化中常常會遇到困境,但若能把別的社會中一些特質或現象分析清楚、介紹給我們社會,這些清新資訊的注入,可以讓己文化獲得啟發和創新。
我不喜歡侷限在學術論文的模式中,所以會寫一些報導文學、小說或拍攝紀錄片,以不同方式展現研究成果。
《媳婦入門》是我第一本發表的書,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台中南屯的農村村落在政經社會劇變中,有什麼變的部分和不變的精神價值,例如農村經濟和家庭結構的變化、文化綿延及傳宗接代的需求。
1983 年於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拍攝的《神祖之靈歸來》,是我的第一部民族誌紀錄片,呈現台東排灣族的「五年祭 (Maleveq)」。迎送神祖之靈的五年祭是排灣族部落中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祭儀,藉由竹竿刺球等祭儀活動,呈現部落的結構理念和驅禍祈福的情感。
在五年祭中,我第一次見到女巫師。雖然排灣族不是母系社會,但巫師一定是女性。排灣族是長嗣繼承。若是長嗣是女的,她掌握的權力之大、背負的責任之重超出想像。在五年祭中我看到女頭目和女巫師密切合作的場面。
後來我接觸到屏東排灣族古樓村女巫師儀式中繁複深奧的唸經和唱經。我很幸運地遇到一位屬於祭儀創始家族的女巫師,知曉祭儀傳統,不只會唱唸也會解釋這整套經語。加上排灣助理柯惠譯很有耐心地協助,我們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記錄、翻譯和解釋排灣古樓女巫師有固定結構和語句的入神唱經文本,希望把這整套快要失傳的經語保存下來。
 身為人類學家,研究的樂趣或未來的夢想?
身為人類學家,研究的樂趣或未來的夢想?
人類學這門學科很有意思,可以親身感受不同族群的文化差異,然後去找差異的原因。這差異現象和原因若找到了,就是自己的體會和發現,會有很大的快樂和滿足。我很喜歡到處跑,和不同的人互動。旁人看了可能會覺得很辛苦,但我樂此不疲。
另外,現在有許多祭典儀式、經語都快要失傳,年輕一輩的原住民知道我們之前做田野調查時,有用影片、錄音等方式,將前人怎麼做祭儀、女巫怎麼唱經保存下來,會來跟我們索取,我們也會主動提供給他們。這些資料都放在《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網站中,從 1984 年開始累積,應該是台灣人類學界採集數量最多的影音資料,任何人若有需要都可以直接查看。我希望這麼美好的文化能讓更多人欣賞、理解,並傳承下去。
我希望,可以讓社會關心我研究的人群。
我的研究內容多聚焦在噶瑪蘭和阿美族,這是台灣社會中較少被注意、理解的族群,我想透過研究發表讓更多人知道,這些原住民族是誰、有什麼樣的文化?特別是噶瑪蘭族,只剩下 1300 – 1500 多人,當未來一位一位長輩走了之後,這個族群就將消失了,可能再過十幾年就沒有人會說噶瑪蘭語。特別是其傳統上母系社會文化與語言的消失,是人類無法彌補的損失。
幸好 2002 年噶瑪蘭族被政府正式認定為原住民第 11 族,有了名份存在,族人就更有向心力共同傳承復振這塊「招牌」,整個邊緣化的部落逐漸有資源進入,其內部彼此間也有更多互動。
例如,原本噶瑪蘭族的 kisaiz 成巫儀式,因為戰後經濟衰退及改信基督宗教的影響,讓這個儀式在 1960 年代逐漸失傳,女巫們也漸漸失去在家族及部落原來的中心位置。
但現在噶瑪蘭人意識到 kisaiz 是他們獨特的文化,中老年人對其歌舞記憶猶深,於是這套神秘的儀式歌舞變成是噶瑪蘭族人向大眾介紹時,顯著的與特有的族群文化「標籤」。 1987 年正名運動時族人和女巫開始聯手再現 kisaiz 成巫儀式,並轉變為劇場展演作為爭取權益的工具,到現今成為宜蘭傳藝中心每年表演的重頭戲,而讓大眾更認識其獨特的文化。

圖│劉璧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