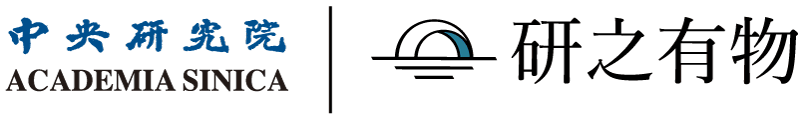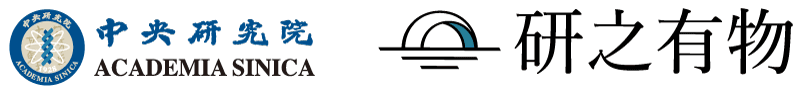看到「巫師」兩個字,你的腦海浮現什麼
電視節目裡,名嘴天花亂墜地誇飾「巫師」的神秘力量,資料來源多半是網路搜尋、口耳相傳,鮮少透過學術性的田野調查,或與族人面對面請教,來了解巫文化的真實涵義。
在中研院民族所胡台麗、劉璧榛的主持下,「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究群定期舉辦討論會與研討會,邀請國際與國內各領域的「巫友」交流,從台灣原住民族出發到世界各地,由不同角度解析不同區域的巫文化。本文以「排灣族古樓唱經」與「噶瑪蘭族 kisaiz 成巫儀式」為例,一同了解當代的巫師究竟做些什麼。
排灣族古樓唱經:提醒族人不變的文化價值
受到現代化與經濟衝擊,台灣許多原住民離開部落,到了都市尋求發展。經歷社會變遷,巫文化仍然保存神祖靈想傳承給後代的精神,例如排灣族古樓村女巫師執行儀式中的唱經 (marada) ,神祖靈會在唱經中附身女巫,透過女巫的口,唱出神祖靈的旨意與教誨。

圖│胡台麗提供
排灣族的巫師皆為女性,稱為 puringau 或 marada ,在各類祭典儀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女巫唱經時手上會拿著桑葉,一邊搖動桑葉、一邊唱經,桑葉裡還會放豬肉條,面前也擺著削了一些豬骨的祭葉祭品。
上方照片中,祭葉祭品和生豬祭品的中間,有一個巫師箱袋,巫師箱袋裡面有巫珠、小刀和豬骨。在最隆重的唱經儀式中,會殺豬並排列肉塊來象徵一整條豬,肉塊皆挑選豬體右側上方的部位,因為族人認為是比較好的部位。以豐盛的豬為祭品,希望換取神祖靈的福庇。

圖│研之有物
古樓的唱經 (rada) 文本非常嚴謹,整體架構是固定的,所有要成巫的女子都要能背得起來這一套唱經。過去未曾有人花精神力氣研究唱經的內容和含意,但胡台麗在研究助理柯惠譯協力下,一句句請教女巫師,花了十幾年的時間翻譯,釐清唱經的意思與脈絡。
研究唱經雖然很辛苦,但可以從中抓出排灣文化的特質,例如神祖靈的概念。
排灣族女巫唱經時處於「入神」狀態,神祖靈會附身透過唱經傳達旨意。入神的女巫師應該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在這情況下,經由女巫師之口,竟然可以唱出一整套超長的經語,有時需一、兩個小時。女巫師說:「不是我,而是神祖靈在唱。」
唱經各段落開頭,是各個神祖靈以第一人稱現身。其中最特別的是,「家」和「村」都是人格化的神祖靈,並非只是建材構成的無生命房子,或表示地域範圍的村子。
排灣族的神祖靈中,有不同領域的創造者,所有祭典儀式皆是為了祈求這些創造者給族人福氣。世間的人只能不斷呼求,殺豬獻上最好的貢品,讓神祖靈有可能來垂顧自己。創造者要怎麼決定你,都是創造者的決定,充滿由上而下的支配性與規範性。
例如,在「元老唱經」的各節中,元老們告誡世人「不要運用強力、濫用靈力」,亦即不要自以為很有力量而勉強行事。
當你們在圍籬外(外村)惹禍犯錯、遭受驚奇窺探時,我們(元老)會不知要如何處理,讓你們脫困。──排灣族古樓唱經,第三章「元老唱經」
噶瑪蘭 kisaiz 儀式:重建部族的自信心與向心力
kisaiz 是噶瑪蘭族的成巫儀式,受到台灣戰後經濟衰退及族人改信基督宗教的影響,於 1960 年代晚期漸漸消逝。但 1987 年之後,族人為了向台灣大眾介紹噶瑪蘭族,展現其文化獨特性並推動族群正名運動, kisaiz 被改以戲劇展演的形式被搬上各種場合。

圖│劉璧榛提供
但要舉行 kisaiz 並不容易,在日本殖民時期噶瑪蘭女巫 (mtiu) 都不敢明示自己的女巫身分,怕因聚眾與消費食物(聚餐)被懲罰。因為舉辦一次 kisaiz ,部落要耗費相當多米食,還要摘野菜、打獵,是一件很盛大、很花錢與捲入眾多人力的事,過去日本人要控制物資與人力用來作戰,所以嚴厲禁止。接著,對戰後時期 1950 年代的族人而言,要辦 kisaiz 經濟上也相當吃緊。
加上花蓮新社部落中的教會認為「泛靈信仰」和「基督信仰」彼此衝突,族人不再讓家中的女孩舉行 kisaiz 而成巫,也不再公開參加女巫集體進行的 pakelabi 治病儀式,甚至儀式所需的蘆竹葉 (baRden) 也會被故意拔除,讓女巫無法順利舉行儀式。
但隨著 1987 年解嚴之後台灣政治氣氛轉變,加上資訊網路發達、偏遠地方公路開通影響,噶瑪蘭族人認知到自己在社會場域中必須要有發聲的位置。
若要爭取噶瑪蘭成為被政府認定的一個族,要有證據顯示自己有不一樣的語言、文化和儀式。
噶瑪蘭人開始思考,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族有什麼不一樣?其中 kisaiz 就是最獨特的代表文化,尤其是在屋頂上跳舞呼喊女神、直觀連結天與家的概念,是其他台灣原住民族所沒有的。
為此,少壯的噶瑪蘭人開始重新學習如何舉行 kisaiz ,也找部落中的資深女巫協助,因為只有女巫知曉傳統巫文化。當 kisaiz 從傳統的成巫儀式,轉變為展演給大眾看的文化劇,部落中的教友和女巫,又有了重新溝通、交流、凝聚向心力的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