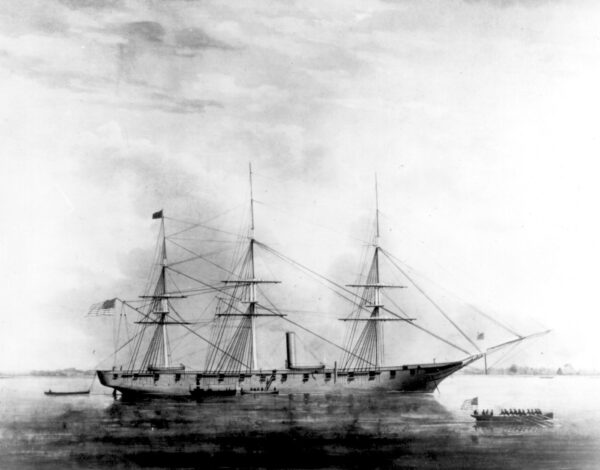圖│劉崇生
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文學」,發軔於中國封建帝國末期,並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間逐漸制度化。1902 年,慈禧太后針對甫成立的京師大學堂進行改革,改革提出的章程列出了文學科,所包括課程有:儒學、歷史、古代思想、檔案學、外國語、語言學和詞章等。
而今日所稱的「文學」,其原型便是文學科下的詞章這一概念,包括詩學、詞學、曲學、文章學、小說學等。
這一設置結合傳統中國小學研究、和西方浪漫主義以降的審美實踐,為現代文學概念首開先河。一種以修辭和虛構為載體的「文學」逐漸為眾所公認。儘管採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文類,或奉行由現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話語,中文現代文學與傳統概念的「文」和「文學」之間的對話依然不絕如縷。
今日所定義的文學──小說、詩歌、戲曲、散文等,以現代白話文為標準的文學學科的建置,是在 1920 年代以後才開始的。
我們所理解的文學,是一個被發明的學科,而其歷史,也不過百年的時間;但王德威認為,在 21 世紀的今天、在臺灣的學院教育裏頭,「文」的定義與討論,其實逐漸出現了侷限性。
王德威強調,他想要提倡與敘述的,是一個廣義的文學觀,但在此之前,他想要先回到「文」這個字本身,藉由觀看「文」這個字的形體,回到華夏文明的傳統去探看「文」所隱含的意象。

圖│維基百科
從「文」的甲骨文來看,是一個錯畫的樣貌,有各種痕跡交錯所形成的圖樣;而在時間的流逝過程中,這個文字被有心人重新建構,演變成一種裝飾、圖飾的意涵;並持續被推衍成形式、文化、文明的意義。而「文」被定義為語言、文章──在審美或唯美定義下的文學的觀點,是到了中古三、四世紀後的事情。
總的來說,「文」有其靜態的意義,如語言、文章;同時也有動態的、屬於日常生活形態的意義,像是文化、文明。
而這些豐富的定義,都是廣義的「文學」的一部分。若今日的學院教育,只以小說、詩歌、散文來解釋文學,那似乎是侷限了「文」所蘊含的豐富的、廣義的多樣形貌。
王德威說,文是審美的創造、是知識的生成;用比較傳統的眼光來看,則亦是治道的顯現。推而廣之,文學就是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從一個地域到另一個地域,對「文」的形式、思想和態度流變所銘記和被銘記的藝術。
換句話說,面對文學,我們不僅只依循西方模擬與「再現」(representation) 的觀念,也仍然傾向將文心、文字、文化與家國、世界做出有機連鎖,並且認為這是一個持續銘刻、解讀生命自然的過程──是一個發源於內心、並在世界上尋求多樣「彰顯」(manifestation) 形式的過程。
正是在對「文」這樣的觀察下,我們面對臺灣文學與歷史的關係,有了更多元的認識。在原住民與新住民、移民與遺民、殖民與後殖民的多重脈絡之間,臺灣文人與庶民對「文」學的建構和解構,自然有別於大陸傳統。
本演講接著從:「文白之爭、文體之辯、文化之別」三個子題來看待過去百年臺灣文、史變遷的脈絡,以期為目前劇烈改變中的臺灣歷史與臺灣論述,提供持續思辨的視野。
「文白之爭」的歷史
文白之爭是從 2017 年秋天以來,文學界及社會公眾爭辯不休的話題,而在各種關心臺灣未來語言或文學教育的爭論裡頭,都將焦點放在最淺白的文字語言、或教科書上的問題。
但王德威認為,作為文學研究者的我們,應該將眼光放得更遠;過往的文白之爭,或有失之膚淺,因此他更想爬梳臺灣文化、文學之源,經由對「文」的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挖掘爬梳,而能使這個論述有更深一層的體悟。
對文白之爭的來龍去脈,王德威從 1895 年的甲午戰爭開始談起,在臺灣割讓給日本後,在地知識、文化界面臨了空前震盪;清帝國的政治統治儘管倏然而止,但臺灣與中原文化間的傳承卻難以一刀兩斷。乙未之後,島上的有志之士展現了強烈的抗議姿態,要捍衛自己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傳統。因此在 1902 年,臺灣中部的古典詩人如林獻堂、林幼春、葉榮鍾等,成立「櫟社」。

圖│林寫真館,1919 年 6 月櫟社總會及臺灣文社理事會合影於瑾園
王德威提醒,當中國歷經五四運動,展開一場盛大的白話文運動的同時,彼端的臺灣則有櫟社這群文人,以他們個人的文化修養,延續漢文的命脈,這個傳統與精神,不容忽視。
1898 年,兒玉源太郎就任臺灣第四任總督,熱心推動各項文化政策,更舉行「揚文會」企圖藉詩文唱和方式達到懷柔目的。此般由殖民政權最高統治者召集的詩會,往後形成了一個小傳統,一直持續到 1920 年代末期。由傳統中文到帝國漢文,臺灣「文」學的改變,已然發生。而在日語作爲國語的教育日漸普及之際,留學北平的臺灣青年張我軍受到五四運動影響,於 1924 年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對準臺灣的「不良老年」展開猛烈攻擊。對張我軍而言,臺灣現代化的意義在於青年與老年、改造與沉淪的對抗。放諸文章,就是白話文與文言文、新文學與舊文學的對抗。
由張我軍等人所掀開的臺灣語言及文學之論述,烽火一燃,演變為鄉土文學與方言使用之論戰。 1930 年,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從左翼角度強調臺灣話與文字合一後,可讓農工基層便於閱讀及使用,引發正反兩方的文學論戰,是為臺灣文學歷史上著名的「臺灣話文論戰」。
王德威於此提到,黃石輝的姿態及其政治立場,其實可能應和著當時中國左翼的漢字拉丁化運動。早在 1920 年代末期,瞿秋白等已經大力提倡「文化革命」,首要之務就是廢除中國文字。在這個意義上,黃石輝倡起的鄉土文學運動,其中所蘊含的左翼能量,往往被我們忽略。
而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複雜的脈絡裡,各種文化的、文學的脈絡交織下,形成了今日我們對──什麼是臺灣的白話文、什麼是臺灣的文言文──這樣一個議題,糾結又難解的狀態。
王德威提醒,「言文合一」是 19 世紀以來國家主義論述下的產物,又因左翼運動放大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利器。據此,「有用」的語言被視爲純潔透明的表意工具,直通文字、文化、以迄民族國家精神。多年以來,「我手寫我口」之類觀點所内蘊的意識形態迷思、及口語/書寫盲點不斷遭到質疑。對此,中研院學者如陳培豐等人也呼籲:
我們需正視臺灣語文現代源起的複雜性,至少包括古典中文、日本帝國漢文、中國白話文、日本「國語」以及臺灣話、臺灣話文。
這些臺灣語文的活水源頭,需要更細膩的解析。
王德威接續說明,不少熱愛臺灣的文人學者,雖然不以五四意識為然,卻不自覺地發揚五四時代由胡適、陳獨秀等所發起的白話文運動。他們對文言與白話的二分法——視前者為封建糟粕,後者爲進步象徵——竟然似曾相識:他們其實繼承而非拒絕了五四、甚至中共左翼傳統。更令人深思的是,推動臺語拉丁化的學者,同時與帝國殖民和全球左派的語言策略形成應對,彷彿經由文字語言的統一操作、擺脫雜質,即可形成有效政教機制。最近的文白之爭,仍然延續此一辯論。
在文白之爭的事件上,王德威認為,研究者們應該是超然的。他建議可以以歷史的眼光,反省如此繁複的課題,不應該化繁為簡,使得議題的爭論極端化。王德威也說,尤其身在學術的場域裡頭,文/言的複雜與論述,實有更多空間、更豐富的歷史資料能夠令我們用細膩的方式探討。
文類之辯:寫實主義、現代主義
王德威從文字不同的表述方式談起,藉由歷史的回顧,談論過往的文白之爭,並給出了提點。而由文字組成的文學作品,則進一步有了不同理論及文學主義的表現。
臺灣文學的文本,其文類表現的兩大主軸,即為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
寫實主義是以描摹人生、反映現實為目的,這一流派於 19 世紀由歐洲經過日本傳到中國,成爲最重要的文學風潮;到了 1930 年代,寫實主義沾染了政治色彩,又成爲批判當下、鑑照意識形態正確性的法門。
對彼時的知識分子和文人而言,「寫實」相對於蒙昧不義,充滿解放和啓蒙之意義。臺灣文學史上重要的作家,如賴和、楊逵、呂赫若、吳濁流、葉石濤等,都以寫實主義的傳統,在臺灣文學洪流中留下難忘的創作。王德威特別強調,對這些臺灣文學的先輩,必須以虔敬的心情,對於他們在銘刻臺灣現實經驗的種種努力,給予最高的敬意。
但王德威也提到,除了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同為臺灣文學發展重要的理論與表現手法。因王德威認為,現代主義之所以為現代,正是出自於對時間、文化、生活經驗其產生斷裂後的危機感;或是對於道統、主體存亡、絕續等的焦慮心情。而這些作家大膽在語言上進行實驗,並經過文字風格的重新排比、題材的大膽突破,所展現出來的文字風格,相較寫實主義的作品,現代主義有了很不一樣的表現與閱讀經驗。
而對照臺灣所經歷的歷史情境,王德威認為,比起寫實主義,現代主義以困頓、荒誕、內向化的敘事手法,或許更能體現這個時代種種的脈動與徵兆。作家如翁鬧、劉吶鷗、楊熾昌、林亨泰、紀弦、李渝、等,以他們獨特的寫作方式,為現實營造豐富的想像氛圍。
這兩大寫作傳統──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所匯集、展現出的龐大的書寫勢力與豐富作品,是臺灣文學有別於其他華語社群,在文學歷史上做出最重要的呈現。
文化之別,衝撞如同板塊運動
文字在不同的文法及語句形構下,有了文/白之別;由文字組成的文章以不同書寫手法的表現,而有寫實/現代主義之分;再進一步擴張「文」的意涵與形態,則有了文化之建構。
王德威認為,談論文學、文史的時候,無法不談論文化;而提到了文化,他則欲將這兩個字置放在更長遠的歷史脈絡中來論述。他提到,臺灣的歷史,在千百萬年以前,只是一個沖積而成的盆地;而後歷經造山運動、蓬萊運動等,令這個島嶼在山風海雨中飄搖變動。而我們的先民來到這個島上留下痕跡,而建構了不同的文化。從原住民開始,歷經殖民、移民、遺民等各路足跡,各種文化匯聚,形成了今日我們生活所在的島嶼文化生態。
來自各方的民族雖同屬南島語系,但在語言文化、社會組織上都顯現繁雜多的面貌。比起這座島嶼千萬年的地質歷史,漢人——以及其他短期的殖民者——在臺灣的四百年的墾殖,毋寧顯得短淺而卑微。但王德威說,這四百年卻帶來前所未見的政治擾攘、文明興替;殖民、移民、遺民的勢力你來我往,以各種名目,表述想當然爾的歷史。
國族的、地域的、族群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力量擠壓衝撞,其狂野之處,竟像地表之下,那千百年來不得稍息的板塊運動。
臺灣在明清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舊的山河猶待重返,新的土地也有待開墾。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談「花果飄零」的悵惘,或是「靈根自植」的期許,臺灣所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時至今日,臺灣仍在一個劇烈的、文化生態的、板塊運動的過程當中,這是我們生處的環境,充滿危機,但同時也滿溢生機與轉機。王德威提醒,作為臺灣人文的學者及研究工作者,必須對這樣的現象給予重視,並有更深一層的思考。
新世紀以來的臺灣論述充滿求新求變的企圖,衍生層層張力。越是要和「前朝」劃清界限,越顯得去古未遠;「亞細亞的孤兒」發現自己原來是「臺灣之子」後,老牌血統論、身分論的幽靈卻仍揮之不去。我們在各種信念及文化價值之間糾結不休,卻仍然對自己的定位、以及何去何從的可能,有著無數的疑問。
於此,王德威提醒,我們若將這些疑問,置放在一個更寬廣的華夏文明的歷史宏觀中,則或許,臺灣的問題,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般不可解。過往的華夷之辯,在時代的演進中或成了華夷之「變」,這樣的變化與變動,持續在你我各方之間進行。然而,在這個移民和遺民組成的廣泊世界中,是易代、是他鄉、是異國、是外族——誰是華、誰是夷,身份的標記其實游動不拘。
不同陣營的群眾,在這個世代下的對話與交鋒,放在千年的歷史演進來看,也不過是千百年的板塊運動中某一次的顯現罷了。
我們如何放大歷史的心胸,放寬歷史的視野,去容納、且細心地處理這些文化之變、文化之別,這是我們所面臨的共同的挑戰。而華夷的辯證如果仍然有其意義,就應該讓我們理解在一時一地的家國之外,我們必須也無可避免地,將在華夷不斷交錯、擴散的世界裡,規劃並理解我者與他者的關係。
王德威在演講最後提到,「文」學是我們見證、銘刻、參與、想像世界變化與不變的嘗試。斯文在玆的「文」,也是日新又新的「文」,這樣的「文」學將及於未來。
反映在自身,無論自居為移民、遺民、或夷民的後裔,當代臺灣更重要的挑戰首在培養公民;只有守法講信、不為一黨一派之私所囿的公民社會,才能延續臺灣文化的政治命脈。在全球化的時代,知識訊息急劇流動,空間位移、記憶重組、族群聚散、網路穿梭,不斷考驗「何為公民」、「公民何為」的定義。王德威說,這是知識分子、研究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繼續讓更廣義的華夷之變,在臺灣的場域裡,引起更多的辯論,共同探討這塊土地的出路。
觀看完整演講影片: